摘录🔗
“柯克兰的研究发现提出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的问题,即她研究的浪漫小说作家中,绝大多数女性在尝试创作浪漫小说之前,都曾是狂热的浪漫小说读者。这些女性中的一部分人声称,她们是为了强化与浪漫小说阅读行为相关的幻想体验,因此才转向创作。但另一部分人则是出于新获得的自信(她们将其归因于阅读浪漫小说),并且因为这一自信催生了想要为其他女性提供快乐的欲望。由此看来,阅读浪漫小说至少让一部分女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她们愿意在公共场合上有所作为、畅所欲言。这类女性于是购买了自己的文字处理机,将先前的缝纫室改为了书房,并要求拥有自己的时间,但现在不是为了获得阅读的快乐,而是为了完成她们自己的工作——她们的这种种行为显然已经开始从本质上挑战传统家庭的权力平衡。”
“但是,就如很多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她们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呼吁在学术界这个享有特权的空间中推进这样的项目,本身就非常成问题,因为那样的呼吁几乎无可避免地基于一种陈旧的精英主义——它假定了女权主义知识分子这一个群体完全了解什么是最有益于全体女性的。在这一语境下,安吉拉·麦克罗比的规劝就很一针见血:学术界中的女权主义者倾向于“低估‘普通’女性和少女……以女性的身份进行着相当独立自主的自我斗争时……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能力”。[52]我认为,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承认浪漫小说的作者和读者本身就难以独是独非地对待性别定义和性别政治,而她们最需要我们这些在其他领域奋进的人给予支持,而非批评或指引。”
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最根本的差异,不在于作者,不在于内容,而是对于作品的定位。
类型文学的作品是文化商品,它具有商品的一切属性:应该为创作者盈利,应该让购买者觉得“有用”。类型文学的出版是“半计划出版”,即经过市场调查,摸清读者的需求和爱好,以此为标准对作品进行一系列甄选,并最终将书送到受众手上。
用一手推动浪漫小说在美国社会流行的“营销编辑”梅西(W. Lawrence Heisey)的话说就是:“在策划促销宣传活动时,产品本身的品质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具备找到受众或消费群体的能力,并找到一条可接近受众的道路……”
当然,梅西的话说得还是夸张了,一旦类型作品大量出现,为了脱颖而出,品质当然还是重要的。但是这里的品质,仍非我们寻常意义上认为的作为文学作品的品质,而是作为文化商品的本质。两者可能重叠,但大概大部分时候是两回事。这一点大概取决于读者——如果该类型文学的读者普遍具有良好的文学鉴赏力,那么文化商品仍可以具有文学作品的品质。也许可以这么说,作为文化商品的类型文学,读者也以“购买”的方式参与了其构成。
而严肃文学则是“无计划出版”,即使是经验非常老到、眼光非常独特的编辑也无把握,一部文学作品究竟是否能在出版上盈利。
因为严肃文学不是商品,它不标出价格,也不标出作用。就像在连锁超市上的角落摆上一瓶意义不明的瓶罐,不能指望谁会去买。
严肃文学,读者无法参与到其内容的创作中,他无法对作品本身造成任何影响。作者不会因为读者不喜欢be而刻意设置结局,不会因为读者的喜好或需求改变作品本身。在内容上,它是完全附属于作者的。
严肃文学不是摆在超市里经过加工,触手可及,开袋即食的商品,它更像是一座矿——你需要一定的工具,费一定的功夫,你才能把它挖出来。
两者本身是否具有什么高低,是否一方是“阳春白雪”、一方是“下里巴人”?我想这倒不必,也毫无意义。虽然都冠以文学的名义,都是用文字书写故事,但两者根本不在一个赛道上。至于阅读它们的读者,就更没有什么高雅与粗俗之分了,大家都是喜欢读故事的孩子而已。
“ 尽管美国社会鼓吹捍卫人的个性和自由,但它相当成功地强制其女性成员提供必要的恭顺。这个文化通过采用严格的社会化程序、制度性习惯以及对逾规越矩的言行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惩戒,促使女性只从社会和制度角色这一维持当前生活机制的关键所在的角度来看待女性气质。
故而,当女性把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视为一种手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抗文化强加予她们的角色时,话语本身却通过把这种角色描刻为一种可随心所欲且受个人掌握的个体选择,而非外界强加的必行职责(necessity),进而极力强调它的可取之处、合乎常情和百般有益。
当浪漫小说的神话式结尾侵蚀了其用小说笔法描写女性个体遭际的现实性时,这种文学形式事实上重申了其基底文化(founding culture)的信念,即女性的价值并不在于她们独一无二的个人品格,而在于她们的生物学同一性(biological sameness),以及她们所具备的能力——承担养护和复原他人这一重要的角色。”
虽然创作和阅读浪漫小说有助于创建一种女性社群,但这个社群成员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这是讲故事这一行为量产化和资本主义组织化后的特性。由于这种对抗行为是通过一本书来实现,由此势必会涉及阅读本质上的私密和孤立体验,因此这些女性从未聚到一起分享想象中的反抗体验。
或者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们没有一起探讨过最初让她们需要浪漫小说的那种不满。这些女性只在象征性的层面团结一致,而且这种团结还是以一种调解的方式出现于个体家中的私人空间里,并被归入在文化意义上不那么重要的消遣活动范围之内。她们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挑战父权文化如下主张所导致的女性彼此之间的隔绝。这种主张声称,女性从未为养活自己而在公共世界中从事过工作,而是作为男性的财产和责任共生地生存着。
总之,当我们从读者本身的角度,也即从一个视异性恋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为理所当然的信仰系统中考量阅读浪漫小说这一行为时,它可被视为一种温和的反抗和渴望改革的活动,是由于制度无法满足女性情感需求这一缺陷而成为势之所趋。于是,阅读对她们而言就是一个认可和抗争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上述缺陷先是得到了承认,但随后又被部分推翻了。因此,史密斯顿读者才声称,阅读浪漫小说是一种“独立宣言”,以及一种向他人宣布“这是我的时间、我的空间。现在让我一个人待着”的方式。
笔记🔗
在《北美殉道者花园》中有一篇短篇《布鲁克教授生活中的一段插曲》,里面有作为文学教授和创作者的布鲁克教授与一名女性(大概是浪漫小说的读者)的对话。那一场对话让我印象挺深刻的,现在想起来,其实那可以算得上是严肃文学对类型(通俗)文学的一场忏悔。
“你们在里面干嘛?”布鲁克问,“在协会里。”
“我们分享。”
“互相借书看?”
“对,”鲁思说,“也做其他的。有时候我们互相读给对方听,谈论人生。”
“听着像是个交心治疗小组。”
“你们写书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鲁思说,“让人们团结到一起,帮助他们度过自己的人生?”
布鲁克不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写书,拿不准自己的动机是否经得起这样的审视。“让我听听你写的诗吧,鲁思,你寄给迪龙的那首。”
“好吧。”她开始背诵那首诗,布鲁克随着刻意而直露的韵律点着头。他几乎没有听清诗中在说什么,他在想他所想过或者说过的,都根本不能让一个女人想要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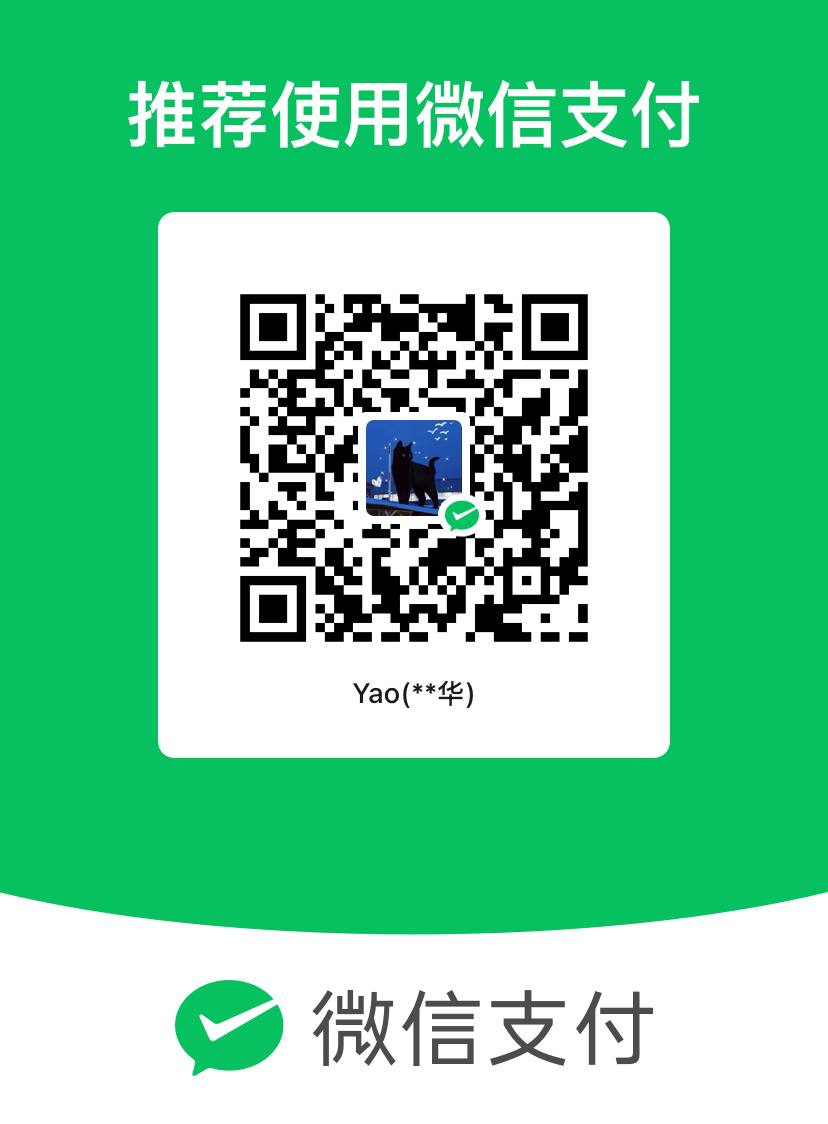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