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安稍稍瞟了那块匾几眼,上面端正镌着三个鎏金大字:归来堂。底下尾款是:熙宁辛丑年王珪笔。是昔日她外祖父所作,写得稳健挺拔,又不失儒雅俊俏,如母亲所说,是外祖父为人。
有时读得累了,或是那金石上蚊蚁般的字眼让她脑袋生疼时,易安便定定望着这三个字入神。这三个字让她觉得心安。
易安常常听母亲说起那素未谋面的曾祖父,说他最爱族中后辈,想必对她更会青睐有加,只可惜。易安不认识那外祖父,自然也不伤心,倒是母亲暗自落泪几回,需要易安好言宽慰才能平复。
月前她收到友人书信,信中写到汴州城沦陷,很是凄惨。昨日城破之景在她梦里浮现,她望见友人满身是血,面色惨淡地沉入那汴河中。她虽不愿相信此梦,但日等夜等,却再也没等到友人的回信。今日离去,两人想必是再无相聚的可能了。
遥想当年汴州城元宵盛会,那时她才不过及笄之年。她抛了明诚(实际上那时明诚要赴宫中与会,她不便参与,不过也无不同便是了)与友人(也是一位与她同龄的少女,一个活泼跳脱、永远长不大的小丫头)约好要去观灯。
两人自御街走起,走到马行街,又折回到朱雀门外街巷。一路上什么都有,击丸的、蹴鞠的、踏索的、上竿的(小丫头说她也想上去试试)、吞剑的(这个她倒不敢了)、耍药法傀儡的、吐五色水的、旋烧泥丸子的、演剧术的、杂扮的、耍猴戏的,不能一一例数。父亲管得倒不严,不过那时她的兴致在诗词,倒不常出去逛的。如今见了这百般杂技花耍,看得眼花缭乱,目不转睛。那小丫头便笑她没见过世面,易安不服气地问她可知道晏几道作词的长短?小丫头装作听不见,打哈哈便过去了。
“夫人,书册金石均已备置妥当。”
夫人?一声叫唤将她从少女时代中拉回。她看向来人,已经不再是那盈盈笑意的少女,而是满脸苦涩的老妪。
易安想着,她的少女时代是什么开始宣告崩溃瓦解的呢?
是从靖国元年么?那一年父亲被定为所谓“元祐奸党”。好在那时也还有明诚和阿公的帮衬,只是被罢官返回原籍。后来天下大赦,有惊无险,父亲得以在老家颐养天年。
是从大观元年么?那一年阿公被罢相,不久病逝。她和明诚两人在汴州从此没了依靠。京城事靡费巨,虽友人百般挽留,她和明诚还是回到青州章丘的老家。
恐怕也不是。在章丘她和明诚度过了多少个花前月下的好时光呐,她与明诚在归来堂中猜书、斗茶,相从赋诗,共治金石之学,又写下《词论》传世,比在那汴州恐怕还要欢快几分。
她的少女时代大概是要在今晚结束,她想。如今金兵将要兵临城下,她在这青州的日子已无以为继,那“尝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生活竟就这样要离她而去。她又是沉沉地叹气几回。此时她才生起母亲那般悲痛莫名的心绪,她竟要离开这归来堂,而且大概是再也回不来了。
易安至今无法理解,那汴州怎会就这样落入那金虏手里?连大宋的皇帝也给人掳了去,实在荒唐!如若说那皇帝与满朝文武是咎由自取,那后宫中的三千宫女,汴州城的千万百姓又是何苦要遭这无妄之灾?易安心中郁闷久久不散。
她自淄州回青州以来,城中时局愈加动荡。诸般光景都令她心中十分不安,但这归来堂的收藏——她和明诚十多年年来的心血却不得不她亲自过来筛选整理,交给其他人她是万万不放心的。如今其中十五车轻便贵重者已装置妥当,准备立即南运,另有十馀间房屋所贮书册什物,准备明年再运往江宁。此外仍有数千书册、金石,但实在也顾不上了。
昨日明诚拖人送来消息,信中叮嘱她勿因小失大,必要时便弃了这些身外之物,速速前往江宁。她很是欣慰,但这些收藏又岂是身外之物呢?这些她在章丘与明诚那些时光的见证,即使抛去这些物件本身的贵重,这一点也足以让她涉险。再者,那明诚十分钟爱的《赵氏神妙帖》,是无论如何也必须得回来拿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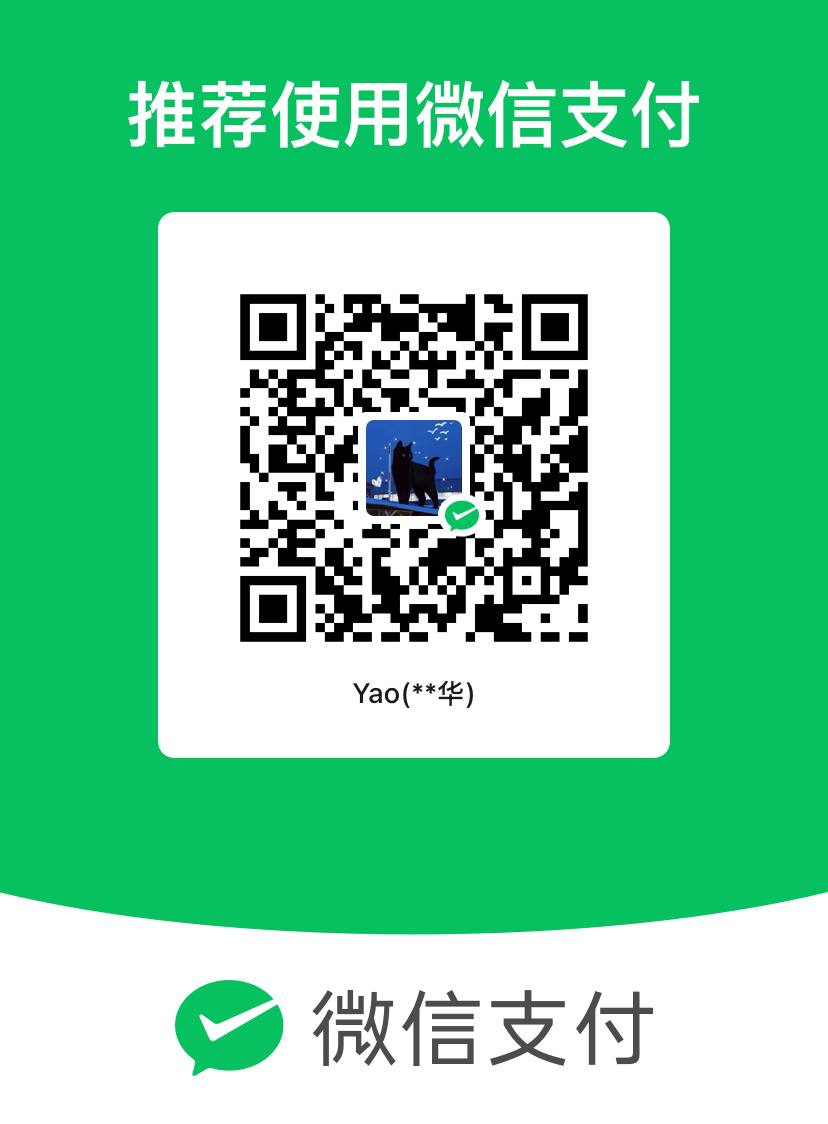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