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其说这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故事,不如说它是我记忆破碎后的一个碎片,但它同时也是我重组记忆的第一块拼图。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它是怎样的已经全靠我们的回忆,这些故事就是我的一个尝试,尝试回忆这些已经随着时间变得无关紧要的事情。它们不太可能是那时候真实发生的事情,记忆时常出错,所以我说它们只是一个个故事;但故事中的人又确实真实地存在着——或者说,存在过,所以我说它们带有回忆的性质。如此这般,我潜入了记忆中。
给人送信可能是一件简单活,但是送一封情书,情况就有所不同,特别是送一封和自己毫不相干的情书。这就像在为记忆的忒休斯之船抛下一个意义深远的锚——不对,我应该用更本土化的说法,那个什么来着?对了,“刻舟求剑”。
用更科学的话来说,这封情书它起着一个GPS定位的作用,尽管它永远不可能那么精确,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方向。在遇见这种时刻的时候,你会有意识地尝试将其记住,把它当作一个“存档点”,每当你回忆起那段时期你就会先从此开始。当情书被塞进我手里的那一刹那,我就清楚地听见存档开始保存的“滴答声”,我毫不怀疑地相信我未来将以某种方式想起此时,以某种方式回到此时。那时我告诉自己应该做好准备,不要使日后想起来显得太仓促和突兀,但我始终立在原地,百无聊赖。我还想问些什么,但人已经走远。
就这样,在2017年11月4日,高二的我站在A3班的走廊上,手上掂着一封沉甸甸的信。应该是沉甸甸的,这里面装着一个人那时候可以拥有的最为繁重的心思,如果那颗心足够真切它会比想象中还要更沉。
我不太确定那天的天气怎样,但我可以尽情给出美好的遐想——也许就像毕业那天我在学校顶楼拍的那张照片一样:那天夕阳给出她最温柔、最优雅的一面,她穿上她心爱的桔红色夜礼服,兴致昂扬地拉上正襟危坐的鳞云(它是一个潇洒自在,来去自如的浪子,少有这般齐整的时刻),跳上一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交场里十分流行的维也纳华尔兹。在舞会的灯光下,整个学校笼罩在一股华贵、慵懒的气氛之中。这封情书的打扮也和这幅光景适宜——一件米白色礼裙,长长的裙摆上用Cadels字体写着:To ZJ。与此相比,我穿着校服的模样真是颇煞风景。
信上的字迹清秀隽永,字体灵动飘逸,虽然只能看见信封外侧上的四个字母,但也足以做出绝对肯定的推测:这封信一定费了写作者很大的心思。只是细细看去,“To ZJ”四个字母像是被笔墨化成的藤蔓所牢牢缠住,想要逃离它可悲的命运却又无法。
拉奥孔群像。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来。
送信那会儿正是每周例行的周六大扫除,打扫已经进入尾声,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最后两个负责倒垃圾的值日生,我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郑季,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ZJ。郑将一封信交到我手上,让我去给A3班的林雪瑶,倒垃圾他一个人来就行。如果是平常,我会饶有兴致地打趣一番郑,但看他沉闷的脸色,我即刻识相地打消了这个念头。A3班就在楼下,而垃圾场在两百米外,显然去送信是更轻松的活。
“等等,你怎么不自己去!”如果能回到那时候,我肯定会这样跟郑说。但真实的历史(“历史”这个词在这显得有些严肃得滑稽,这就是我的目的所在)是我什么也没说,我看着郑提着垃圾桶绕远路从另一边楼梯离开——在我看来是有点蹑手蹑脚,他想绕过A3班去垃圾站。为什么这么做?答案显然不言而喻。
好吧,A3班的林雪瑶?Doesn’t ring a bell.郑好像和我寥寥谈到过几次,是谈什么呢?我也记不清了,我记得清楚的是另一个女孩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对话中,而且郑明确无疑地告诉过我他喜欢这个女孩子——看起来好像大致情节和剧情走向已经很明了,一场总会在校园里上演的老套的故事:
A喜欢B,B喜欢C。一般来说,在这个故事中C往往有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故事情节是会像《罗生门》那样错综复杂,还是会像《俄狄浦斯王》那样命运无常,全取决于C的意愿。当然,A也可以选择不坐以待毙——这封信大概就是A最后殊死的一搏,但迄今为止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这场搏斗的不公平(实际上,这就是爱者与被爱者的不公平),那边是全神贯注、倾其所有,这边是心不在焉,躲躲藏藏。
Any way,在2017年11月4日,高二的我站在A3班的走廊上,手里掂着一封沉甸甸的信。周六晚上放假,除了倒垃圾的值日生,这个点没人会待在教室——确实,只有她一个人在,这个信封的主人。看起来她像是有意挑选了这个时间段,以避过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天教室里的场景也是可以预想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想为这个画面插入一首歌:万芳的那首歌——《在那个冬天的下午,我爱你》。这个画面只有一幕,它是这样的:夕阳提着裙摆迈着轻灵的步子一个纵身跃进教室,桔红色长裙铺满半个教室:窗帘是桔红色的,课桌是桔红色的,黑板报是桔红色的……但她不是,她正坐在夕阳照不见的地方,那个地方昏暗得巧夺天工。她像是在看书,但眼神却不断地向走廊外瞟,那本书看了许久也未翻一页。显然,她在等着什么,而且愈加焦急难耐。无论她在等待什么,不太可能是我和这个信封,但现实就是,来的只有这两样。
(“为爱而受苦的人们,她们的愁相是如此地一致。”)
我暗自叹口气,默默从后门走进教室。踏进教室的一刻,她就像是惊弓之鸟一般身躯猛地一震,随后又艰难、缓慢地恢复平静,但还是以细微的幅度颤动着……她在害怕么?害怕面对接下来可能的命运?她也许一下就知道我并不是她所期望的那个人了,她笃定这不是他的脚步声——她一面为自己能听出他的脚步声而欣慰,一面又为那个脚步声不是他而痛苦——她是在这么想么?我加快脚步,想赶快完成任务,离开这个即将滋生哭泣与悲痛的教室。
“他让我把这个给你。”我把信递给她。
一封情书,我早已猜出这封信的用意——精美的包装,十足用心的字体,写信这种严肃的方式——不是一封情书还能是什么呢?而退回一封没有拆封的情书,这显然代表着拒绝,十分决然的拒绝。郑季收到这封信时的神情早已宣判它打道回府的命运,那张脸上可没有浮现出任何一丝惊喜与讶异,只有沉默、迷惑和淡然。我想,那时爱情的死刑早已宣定,只是受刑的人还未到场。
她接过信来,小心翼翼,像是手里拿着什么易碎的珍贵珠宝。有趣的是,她的神色似乎和郑收到信时的模样无二,大概是为了不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过于失态?不过她很快就会发现的——死刑即将宣告,她将被命运的藤蔓所死死缠绕,为名为“爱”的酷刑而饱受折磨!——拉奥孔群像。我再次想到。
当她发现信封还未曾拆封时,她的身子地整个僵住了一小会。只这一小会儿,世界上所有凛冽的寒风都毫不留情地吹向她,而她的灵魂在此刻是如此赤裸裸,没有防备——她本该有的!在所有与他的对话中他都没有显示出任何意义上的好感,她明明知道这一点,早该为这番无情的拒绝做好心理准备,但爱使她变得盲目,她抱着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希望。这一点希望现在成了千里之堤的蚁穴,她的心防将彻底陷入崩溃。
对于一个对爱抱有幻想的人,这是一次多么残酷的打击!——你将你的心交出,它离开你温暖、舒适的心房,来到那个人的面前,怦咚怦咚热切地想要告诉他你的心意,你说,“外面太冷了,让我住进你的心房吧!多少房租我都愿意!”
但你的心敲了好久,那个人连门都没开!但你的心却回不去了,即使把它强塞回自己的心房,它也不愿意跳动了。也许再过一小会儿,心呜咽的声音就会响起——哭泣与悲痛,就像我早已预见的那样,但出乎意料的是教室里只有难熬的死寂。一支舞跳毕,太阳落到了山的那边,教室里灯没开,夕阳仍有余光,只是过于昏暗。
没有哭声,只有沉默。我做贼心虚一样偷偷瞟她一眼。即使到今日,我也没能分明理解那副复杂神情中所表达出来的心绪。懊悔?坦然?悲哀?如释重负?我甚至怀疑世界上是否有一个词能够描述出那样的神情。如果非得找一个契机来让读者理解她的心情和想法,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那也许会有答案。
“让他自己拿过来给我!”许久,她才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一句话来,一边说着一边把信塞给我。塞这个动作总是粗辱的、强硬的,她也不例外,特别是当她还处于某种愤怒之中时。但她下意识中仍然小心翼翼,这封信对于她仍是珍宝,尽管已经没有买家。
我不太确定我此时该说什么,安慰?劝告?解释?无论怎样做,似乎都显得多余。也许她说得对,应该让那个人来做。但是我倏然有些厌倦,我是一个局外人,为什么要让我掺和你们俩的事?你喜欢他也好,他不喜欢你也好,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跑腿的,东西送到,任务完成,要拿你自己拿好了!
我有些懊悔,刚刚就应该这样同他说,现在倒好。我干脆保持沉默,把信又放回她桌子上,她也二话不说随手一撇把信甩飞。信在空中经过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回旋,重重摔在地上,发出一声刺耳的锐响。巴掌打在脸上差不多也是这个声音吧?心碎差不多也是这个声音吧?我拾起来,拍拍上面的灰,兜在口袋里走出了A3班,背后传来呜咽声。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没头没尾——但没办法,我很乐意为读者着想,将故事的前因后果都说得清清楚楚,但我也是在中途才匆匆忙忙加入(说“加入”有些奇怪)这个故事,而且扮演的是一个无关轻重的跑腿角色。我所知实在甚少,如读者所见,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场连续剧中的一幕而已。如果我再多作阐述,那只能是一些不可证实的猜测而已。追忆过往本就是件苦差事——你要在没有线球和宝剑的情况下穿越像米诺斯迷宫一样危险重重的记忆宫殿,一不小心走错一步(就像扣错一个扣子),整个路线就全盘皆错,then,你不会回到任何记忆中的场景去,你会陷在迷宫里的深处,就像上阳宫里的宫女一样慢慢衰老,死去。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我不会做这种危险的猜测。我唯一还能为读者提供的确证无疑的信息是:林雪瑶后来和郑季“和好如初”,两人恢复了告白之前的朋友关系,在各种节日时会互相祝好,朋友圈、qq空间里时时会看到他们互相点赞,在底下评论。那天下午的一切好像都自然而然地过去了。那天的夕阳和云彩不用说,它们每天都在变化,每时每刻都在成为过去;林悲绝的眼神与她近乎无声的抽泣,还有那封未曾打开的情书,也没有理由不随着时间而化为云烟。
我有时候再次回想起这件事,会先想起那封信的去向:它最后去哪了?如果能找到那封信那大概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就能清楚了,这是我欠读者的一个交代。那封情书仅其外观来看已经称得上是赏心悦目,其中的表达如果足够真挚,那么也能为本文增添一份光彩,如果行情好,还能赚取一些读者的眼泪。但现实是生活得继续运转,太多太多新的东西要存放,即使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封信也大概早就被扫入心房里堆满灰尘与蛛网的阴暗杂物间中了吧,到何处去寻呢?你不太可能从其中再找到过去那么一封不显眼的东西。也许它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就像年轻时发烧一般热烈而盲目的爱,随着时间推移就那样自然而然消退了。只是好笑,在这场恋爱悲剧中“跑龙套”的我却对此耿耿于怀,以至于特意写了这么一篇不像样的小说来记住这个可怜的爱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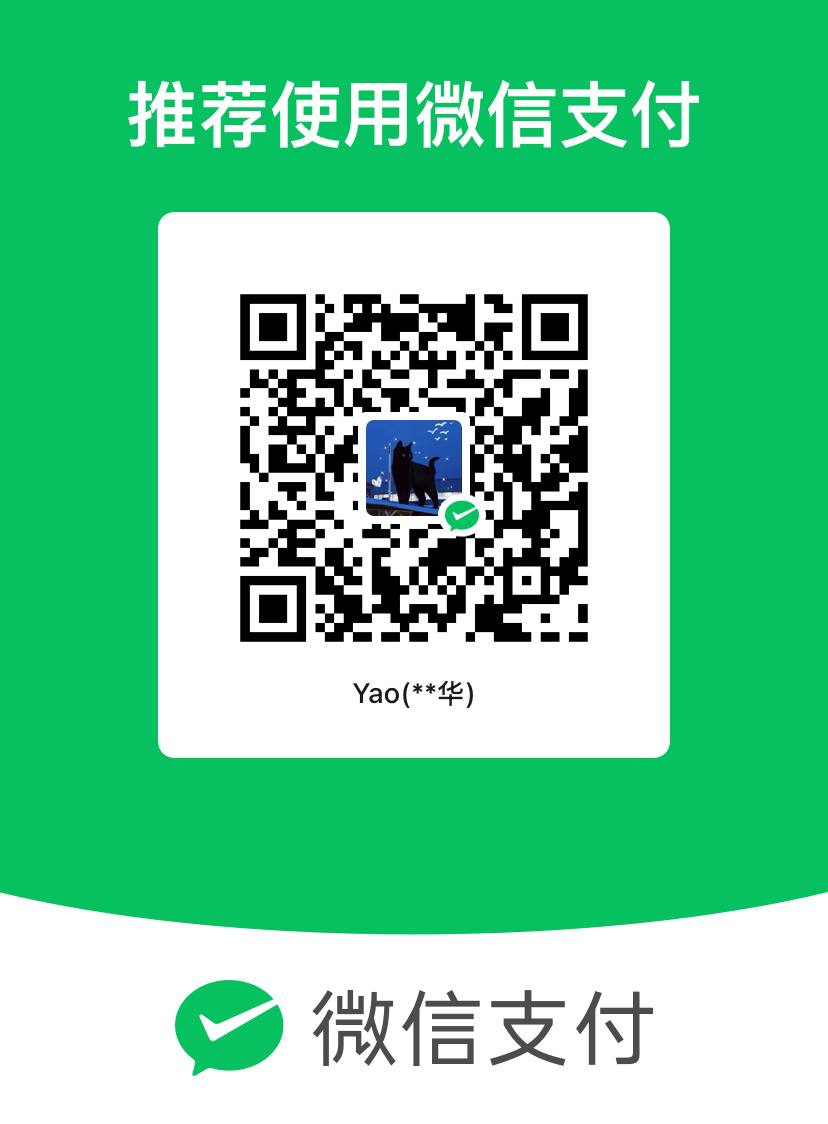
评论 🔗